1995年,我创业失败,灰头土脸回到家乡。
在父母的安排下,我和她结了婚,亲友们都来道贺,说我娶了镇子里最漂亮的姑娘。
我笑笑,没有说话。
如果可以,我是不想娶她的。
她家里穷,书也念得少,空有一副好皮囊却没有什么才气,比那些大城市里的姑娘差之甚远。
和她结婚,意味着我将一辈子囿于平庸。
在这个思想泥古不化的年代,被编排的婚姻,注定是一个画地为牢的过程,我们每个人都想跳脱这个圈子,却还是无可奈何的妥协。
新婚当夜,我站在窗前,一边数星星一边喝酒,她坐在床边,埋着头,有些拘谨。
老旧的白炽灯散发昏黄而微弱的光,几只飞蛾顽固的绕着灯泡飞行,气氛沉闷。
“不休息吗。”临近午夜,她羞怯的开口。
“不了,你睡吧。”我淡漠地说。
她沉默,过了很久才轻轻“哦”了一声,脱下外套,躺在靠里的位置,被子拉得很高,埋住了头。
我看了她一眼,暗自嗤笑。
身后传来低不可闻的哭泣。
我的手轻轻一颤,酒洒了出来。
灯,亮了一夜。
1.
婚后不久,在父母的催促下,我们行了房事,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。
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增进,依旧冷淡,像两个陌生人。
我一心想要重新创业,证明自己能力,每天早出晚归,几乎不和她说话。
她则是挺着肚子做家务和农活,不抱怨也不吵闹,沉默地像块石头。
每天清晨,床头都置有洗净晒干的衣服;晚上回家,饭菜和热水也已经备好。
我觉得别扭,说:你过你的,不用管我。
她说:没事没事,应该做的。
我有些火了,说:叫你别管我,你是我谁啊。
她愣愣地看着我,眸子一暗,转身走出去,身子有些颤抖,分不清是冷还是在哭。
父亲把我拉到院子里,指了指四周,问:看见没?
我环顾一圈,墙上挂着农具,地上铺满晾晒的玉米,井边是盛满水的桶,一切有条不紊。
很整齐啊,怎么了?我问。
混账!
父亲勃然大怒,一巴掌抡在我脸上。我的嘴角溢出鲜血,脸颊高高肿起。
他大吼:怎么了?你媳妇眼瞅着马上就要生了,还每天挺着肚子做脏活累活,你做丈夫的竟然一点也不关心。小兔崽子你还是个男人吗?
我吐了一口血沫,吼道:又不是我要娶她,她爱干啥干啥!男人?你不觉得我他妈更像一只用来配种的公猪吗?
你……我打死你。
父亲怒极,抄起竹耙就是一顿乱打。
声响惊动了她,她摇摇晃晃跑出来,拉着父亲,说:爸,别打了,让街坊邻居听到了笑话。
说完她又过来扶我。
装什么装,不用你假慈悲。
我冷笑,一把将她推开。
她竟是没站住,跌坐在地上,当下脸色发白,冷汗直刷刷地冒。
2.
1996年11月2日,我永远记得那天。
刺鼻的消毒水气味在空气里弥漫,来来回回是身穿绿色手术服的医生,他们戴着巨大的口罩,瞳仁深邃,眉锋如刀,行色匆匆好像即将奔赴一处战场。
我正襟危坐在走廊长椅上,浑身肌肉紧绷。
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,只感觉莫名的焦躁,心乱如麻。
小时候,我最讨厌来的地方就是镇上这家医院,因为这里设施简陋,医术中庸,很难让病患得到安全感。
现在我却不得不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,祈求手术圆满。
时间在焦躁中流逝,直至暮云壁合,医生才摘下口罩,疲惫的从手术室走出。
胎儿没事,是个男孩。
医生朝我招手,示意已经可以进去了。
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,小心翼翼打开门,
产房内,她因疲劳过度已经睡着,眉目温婉,令人怜惜。旁边小床上,一名男婴睡得深沉,模样娇憨。
画面安详,一幅人间。
我长长抒了一口气,浑身的力气好像在这一刻被抽空。我蹑手蹑脚走过去,静静看着她们,眼眶突然有些湿润。
3.
或许是有了孩子,我变得不那么排斥她,虽然还是很少说话,关系也逐渐趋于缓和。
她身子骨弱,每天做农活还要带孩子。
我心中愧疚,就建议她买些奶粉给孩子喝,被她严词拒绝了。
当时她的表情很严肃,向来温婉的面庞第一次露出认真和执着,不容辩驳。
她对孩子照顾的很细致,从每天嗷嗷大哭到蹒跚学步,孩子茁壮成长。
下午回家,还未进家门她就跑出来接我,一脸兴奋地说:孩子会说话啦。
回到家里,,孩子正抱着奶瓶来回转悠,乌黑大眼睛闪烁着光芒,瓷娃娃一般,粉雕玉琢,憨态可掬。
我跑过去,把孩子抱起,捏着他的小手,说:宝贝,叫爸爸。
她也轻声说:宝贝,快叫爸爸。
孩子嘟嘴,奶声奶气地说:爸爸。
我心里高兴,也说:叫妈妈。
孩子说:爸爸。
我指了指她,又说:宝贝,叫妈妈。
孩子睁大眼睛,迷茫地看着我,好半天才咿咿呀呀哼了几下,不知说些什么。
她眼中闪过一丝尴尬,把孩子抱了过去,轻描淡写地说:哪有那么快呀,孩子才刚学会说话,还只会叫爸爸。
我看着她平静的脸庞,突然感觉一阵强烈的酸楚涌上鼻尖,眼眶忍不住泛起雾气。
我怕被她看见,赶紧转身,说:哦,那你没事多教教他,我出去溜达溜达。
4.
2003年,秋。
孩子念了小学,家里开销逐渐增大,她提出要去找一份工作,分担经济压力。我说,不行。
我的反对无效,第二天她就在县里找了份工作。
工作是邻村王芳介绍的,在一家大型娱乐场所做迎宾小姐,薪水可观,据说王芳自己也在那工作。我说,鱼龙混杂,不行。
我的反对再次无效,她很快就去工作了,每天比我更早出晚归。我早晨7点起床,她已经做好了饭;我晚上7点吃饭,她还没有回家。
我说:你这工作太累了,也危险,辞了吧。
她不同意,说:孩子大了,以后花钱的地方也多,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工作。
她说话的时候语气十分坚定,眼神温柔而倔强。
我突然发现我拿这女人没辙了。她多数时候温顺如同小猫,有些事情却又一反常态的强硬,死死捏住你的软肋,让人没有半点脾气。
她工作半个月就出事了,晚上回家,她脸颊红肿,情绪有些低落。
我说:谁打你了?
没有,不小心磕着了,没多大的事儿。她没有看我,埋着头吃饭。
我能是那种招惹是非的人吗?她怕我不信,又说。
我使劲吸了口烟,说:那行,自己注意点。
第二天有人来闹事,大门被人一脚踹开,一群非主流把头发染的花花绿绿,在院子里叫嚣。
我们从屋子走出来,一群小混混立马围上。
我说:你们干什么?
干什么?这臭婊子,花钱买她她不干,背地里偷老子的钱包,装什么清高?一个小混混叫嚣。
她气得浑身发抖,咬着嘴唇倔强地说:我没有。
又有人骂:没有?当了婊子你还想立牌坊?
此时院子外面已经围了很多人,指指点点,王芳也在里面。
喧嚣声吵到了孩子,他握着笔从屋里跑出来,见眼前人皆凶神恶煞,泪水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,嗷嗷大哭。
我让爸妈把孩子抱回去,说:是不是搞错了,我媳妇人老实,就一做迎宾的,不会……
为首的混混打断我的话,指着我的鼻子,气焰嚣张:错你妈逼,你让她给我们几个干,这事就算了。
我说:你他妈再说一句。
你让她给我们干……啊!
我操你妈。我从地上抓起一匹火砖,直接拍在他脑袋上,鲜血从额头一直流向脖颈,狰狞可怖。
一群人有些懵圈,好一阵才反应过来,抄起竹耙、扫把开始反击。
我冲上去,又把一个人脑袋拍出血,然后转身将为首的混混扑倒,任凭其他混混围殴,我只认准他,劈头盖脸地狠砸。
而且只砸头部。
我浑身淤青,额头也破了。为首的小混混更惨,脑袋都快被拍成血葫芦了,五官扭曲,疯狂的尖叫。
不知是谁报了警,警车嗡鸣,几个混混全部被抓走,王芳见这阵仗,当场吓哭了,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交代。
事情真相大白,王芳说人手不够,骗她一起去送酒水,去了才发现是做小姐,几个人围着她就要脱衣服。她不愿意,被人打了一巴掌,跑了出来。混乱时王芳见搁在沙发上的钱包鼓胀,里面钞票猩红,忍不住偷拿了。
警察手一挥,把她也带走了。
人潮散去,她腿一软,扑在我身上,青丝散乱,泪眼婆娑,失声痛哭。
那哭声悲恸,包含数不尽的委屈,仿佛要震碎人的灵魂。
我突然很难受,紧紧抱住她,说:别哭了,别哭了,这工作咱们不做了,好好过日子。
5.
2006年,城市规划朝南扩张,县里决定新建火车站,选址在我们镇。一夜之间,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马路修到了家门口。
趁着这个机会,我利用多年的存款和政府占地补贴的钱,在镇上,哦不,在新城区开了一家建材店。
接下来的几年,生意顺风顺水,我买了好车,住上最好的房子,儿子也转入县里最好的学校。
从未有哪一个瞬间,我如此靠近自己的理想。
和吴月认识,是在一次酒会上, 她风情万种,一颦一笑都足以摄人心魄。当那些低腰抹胸的庸俗女人还在释放情欲信号时,她已经开始述说最亲密的耳语。
她成了我的情人。
吴月是个聪明的女人,不矫情,只要钱,态度明确。说是情妇,倒像是一个拿钱办事的妓女,不给我带来一丝心理上的负担。
只要她不在,我就把吴月带回家,疯狂纵情。像是两只看到奶酪的饥饿老鼠,都想把对方化到肚子里。
我想要phone5。
吴月腻在我怀里,光滑的背脊令人疯狂。
我笑着说:买,你想要什么都买。
吱。卧室门把缓缓转动。
吴月吓得跳起来,赶忙藏进衣柜,我裹紧被子,佯装睡觉。
出乎意料,把手停止转动,弹回初始,门外传来虚弱的咳嗽声。
声音渐远,好像进了厕所。
我慌忙套上衣服,蹑手蹑脚将吴月送走。
折返到洗漱间,她正弯着腰干呕,咳的很用力,脸上是病态的白。
我说:怎么了?
她虚弱的笑笑:没事,可能有些着凉吧。
这样的事情又重复了几次,每次都是有惊无险。
我开始怀疑她是故意不揭穿我,心中愧疚,却更加肆无忌惮。
吴月说:要不你和她离了吧。
我笑道:离了娶你?
吴月说:你老婆指不定也在外面有别的男人。
我脸色一正:别胡说。
吴月起身,走向梳妆台,从放首饰的盒子里翻出一张纸,扔给我。
她说:一不小心发现的,你知道这个东西吗?
纸是反复折叠的,我打开,是一张全身体检报告,密密麻麻的数据令我有些茫然。
我点燃一根烟,说:这是什么?
吴月冷笑:指不定染上了什么病。
6.
给她做体检的女医生年逾半百,资历很老。
我将体检单推给她,说:医生,这是什么病?
女医生神色黯淡,说:肾衰竭。
不是性病吗?为什么会是这种病?来医院之前,我甚至已经找好了律师,只等结果一出来就拟定离婚协议书,怎么……会这样?
我猛一拍桌子,从椅子上跳了起来,说:怎么可能!
医生说:没错的,这份体检单我记得很清楚,我跟她建议过住院治疗,做透析,她……没同意。
我有些癫狂了,大吼:为什么不同意?透析能救她吗?
不行,她现在是肾衰竭晚期,药物已经没办法治疗了,透析只能帮助她延缓病情,除非……换肾,可是肾源哪有那么好找……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院的。
突然感觉一切都很幻灭,风落在叶子上,飞鸟停在空中,世界一点点变成灰色,无数裂纹蔓延,将要破裂。
回到家里,我瘫在沙发上,失魂落魄。
她从厨房出来,说:你怎么了?
我浑身发颤,说:你有什么事瞒着我?
没什么啊,怎么了?她显然有些吃惊。
我大声质问:难道那个体检单不是你的吗?
是我的,我也不瞒你了,你在外面不是有外遇吗?我也一样,咱们互相扯平了。
她突然一反常态,折回卧室去拿了一叠纸,摔在桌上,说:这是离婚协议书和财产证明,签个字吧。
我怔怔然看向那叠纸,扫过几项条款,大意都是她要求净身出户,不拿一分钱,落款处,字迹娟秀,白纸黑字。
她冷笑,说:不用看了,我会不拿你一分钱,他比你有钱多了。半辈子了,终于可以摆脱你了。
说这话时她摆出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,眼泪却已经崩溃,噼里啪啦往下掉。
到现在你还骗我?你他妈生了点小病就想跟老子离婚?我告诉你,我不同意!
我猛地站起,抓起离婚协议书疯狂撕扯。
她扑上来,没抢到,哭着锤我,说:你干什么?我已经没救了!没救了!
我双眼通红,一把将她按住,说:天要你死,老子也要把你救活!
7.
2012年9月17日,我和吴月断了关系,让她接受治疗,在我和孩子的一同劝说下,她答应先住院试试。
我带她去了省里最好的医院,她每天要吃很多药,忍受透析的痛苦,一瓶瓶安瓿敲碎,药液注入她的体内。
2012年10日13日,她的病情一天天加重,每天做透析,虚弱的躺在床上,弯着腰咳嗽。
看着她难受的样子,我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。
如医生所说,药物治疗只能缓解,无法治愈。
我找遍所有的关系,在网上求助,去黑市问。
无一例外,没有肾源。
2012年11月30日,我找到了肾源,兴奋地告诉她有救了。
她倔强的问:来路正规吗?不正规就不要,不能害了别人。
我摸了摸她的头,笑着说:放心吧,对方自愿将器官捐助给需要的人,不过……捐助者不愿意透露姓名。
她抿了抿嘴唇,说:如果……有机会知道,一定要感谢别人。
我说:嗯。
2012年12月8日,手术即将开始,她有些害怕。
我抓住她的手,说:你可得好好活着,以后还要看儿子上大学,当奶奶,抱孙子。
嗯。
她的惧意渐渐消退,脸上浮现一抹明媚,仿佛回到十多年前刚出嫁那会儿,小女儿家一般,不施粉黛,不可方物。
大门缓缓关上,医生将她带进手术室。
要活着,要一起变老。
看着她的背影,我轻声低语,忍住泪水,走向另一间手术室。
医生帮我消毒,换好衣服。我躺在手术台上,明晃晃的手术灯让我有些睁不开眼。
医生敲碎安瓿,注入麻醉剂,向我投来鼓励的眼神。
意识渐渐模糊……
——————
经过这两年的调理,她已经能够正常自如的生活了,虽然生出些许白发,不过依然温婉动人。
限于身体原因,我不能过度劳累,于是找人代替打理建材店,每天陪她。
我们一起做菜,到处旅行,尝试新鲜事物,在朋友圈发照片。夏天在江边散步,冬天窝在沙发上,就着暖气看电视。
今年九月,孩子上了大学。
有时候,看着我身上的疤,她会忍不住落泪,哽咽着说:当初你不应该救我,现在条件这么好,再找一个对你和孩子都好。
我笑着抱住她,说:二十年了,跟你在一起我都习惯了,没有你我怎么过?
我从未后悔做出这个决定,男人一辈子总该爷们一回,这些年我付出太少,亏欠太多。看似完满的人生,其实是因为有令你心安的人在身后默默支持,才能一路坦途。
我们似乎从未经历过爱情这个阶段,那些海誓山盟和轰轰烈烈就像电影和小说般遥远,只是,一路走来的不离不弃,却是如同花蔓与树的纠葛,比任何感情都要来的深沉。
曾经以为的平庸,其实才是最大幸福。
相濡以沫,就是最好。
感谢时光,让我知道我有多爱你。
完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作者:景深
链接: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25537696/answer/65898642
来源:知乎
著作权归作者所有。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,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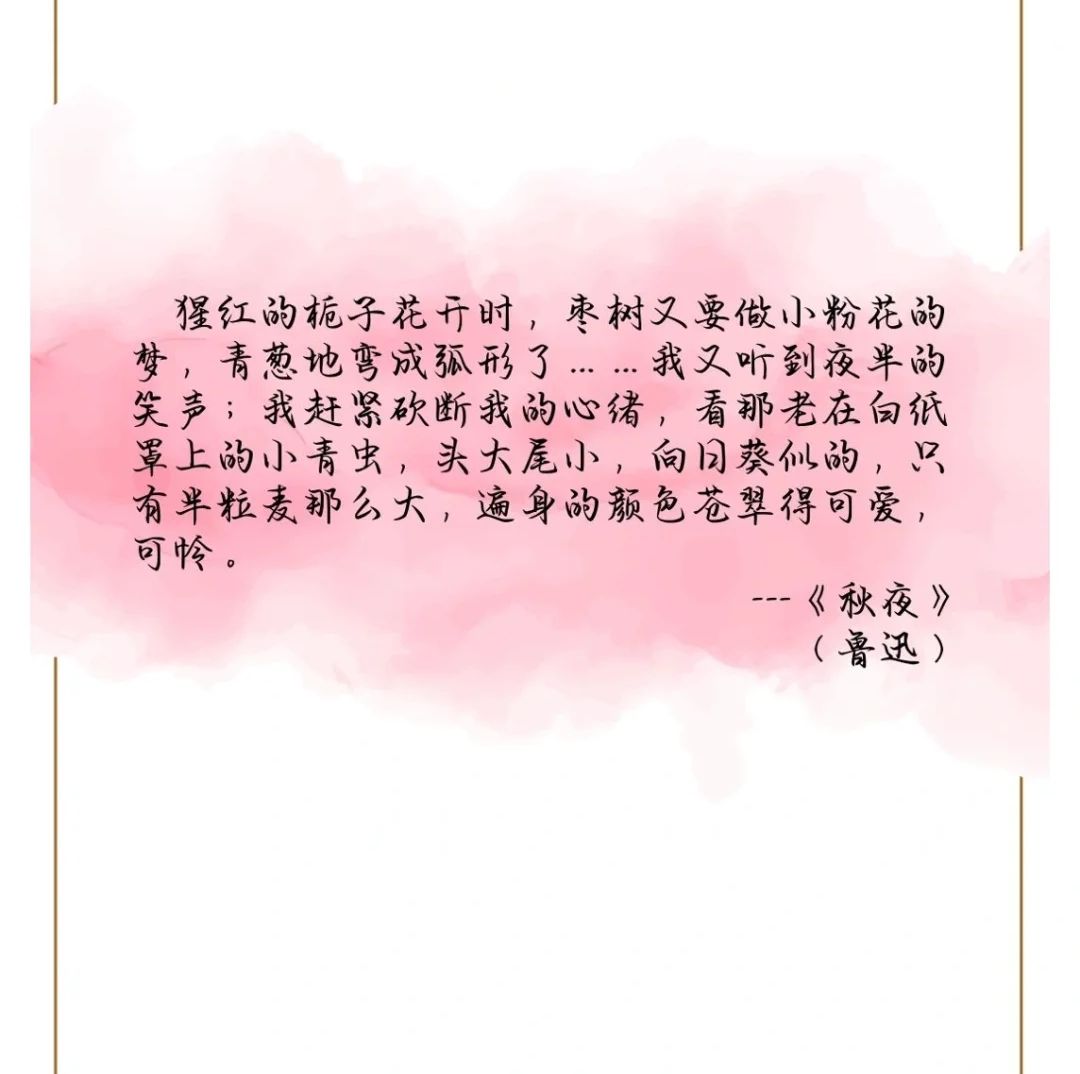
请登录之后再进行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