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忆是个很不靠谱的东西,我常常感觉我的童年是灰蒙蒙的,模糊一片,当我用力去想时,这种感觉会大片大片地蔓延,以至于我的童年记忆有着苍凉的底子。
就让我把脉络分清晰一点,我的记忆里有一个书柜,奶奶拿着这个柜门的钥匙,每次我都是装作好学的样子,轻易地从奶奶的手里得到这个钥匙。然后再把记忆范围放大,这个柜子立在一个曾经有些洋派的居所里,并且一直洋派了很多年,但自从建成以来大多时间它是空的,奶奶像是守着一个古堡一样一直守着它很多年,直至离去。
再说说这个房子的主人,他是我的二伯,与我家前后相邻,这个家当年享受不少尊荣,比如这个洋派的房子,比如人家都在吃窝窝头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吃白面馍,比如第一台电视的到来。新鲜的东西首先的享用更多地出现在他们家。二伯有两子一女,年龄都是相差不大,最小的孩子比我大六岁。年少时的年龄大着五六岁就隔着一大截子,可能一个还光着屁股,另一个就在上小学;一个上大学时,而另一个在工作岗位上。阅历经验层次分明地打在脸上,几乎做不得假,而直到二十岁以后才会渐渐趋同,模糊年龄的界限。所以在他们的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,而且在我少不更事的年龄里举家搬迁去了外地。也许算不上远,五六百里的路程,我一直以为五六百里要隔着绵延无尽的山脉,要爬山涉水如西天取经般。因为他们都极少回家,而年迈的奶奶似乎是他乡唯一的挂牵,因为只有奶奶才能把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召回。
亲戚或者朋友,是需要来回的走动来维系感情的浓度,血缘关系固然是一个天然的纽带,然而少了彼此间的互动,也会慢慢地淡漠。很偶然的一次二伯的大儿子打电话过来,声音中我并没有判断出是谁,他也在问我是谁,很显然的也是感觉声音陌生。我一直很喜欢他,是因为他温和的个性,他对我的疼爱也是十分的温和,毕竟是年龄隔得更远一些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个性很相近,我们都是沉默寡言,不善言辞。我在那个大书柜里翻出来他的日记,并且很不道德地从头看到尾。那娓娓道来的文字一如他的为人。他一直都没有回来,直把他乡当做了故乡。我也常常想,如果我是他的话,我估计也不会回来。一是因为情怯,另一方面是他为人太过于淡泊。我曾经想过给他写信,可最终觉得太过于荒唐。不过我陆陆续续地听到一些他的事情。他曾经有个女朋友,长得非常漂亮。大娘因为女孩在酒店工作心有怨言,说一个女孩子,在一个风言风语的环境里实在不能让人放心。这个感情最终没有得以延续。但是那个女孩树立了一个标杆,这个标杆太高,以至于其她的女孩都需要仰望。他渐渐成为了令人心焦的大龄青年,很多的女孩喜欢她,可他总觉得不入眼。
二伯的小儿子倒是偶尔会回来,他去过很多的地方,好像总是在不同的城市里晃悠。每次回来都是衣着光鲜,他那浑身散发的一种天然的朝气和优越感,这让他格外地与众不同。常常让人模糊地以为他不是本地人。事实上他早已脱离这个圈子,游走于另一个世界。一次他回来带我和杨秀一起出去闲逛,路上给我们一人买了一瓶饮料,我们都没喝过。杨秀偷偷地告诉我,这一瓶好几块钱哩。现在想想就觉得可笑,那时真是井底之蛙。真的,不是他站得足够高,而是我们站的地方太低了。我们一直没什么交集,而弟弟对他的印象就更加的模糊了。弟弟参加工作一年了,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他工作的城市,他知道后,见了面。弟弟给我说起见面的经过时,语调因为生气而有些激昂。很显然他不喜欢这次的见面,弟弟因为他的居高临下的告诫而起了反感。然后弟弟形容他发福后的样子时,我觉得好像说一个陌生人。而他依然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兄长,而那份优越感却让他更像一个领导,却忽略了那么多年的光阴,我们早已经成长,只因他没有看到,所以只当不存在。
我们家的前后院都是他们家,前院的老房子早已经破败得与这个时代脱了节,当年他们举家离开的时候植上满院的白杨,如今也已经高大参天,不知道他们回来会不会感叹树犹如此。后院里原有两颗古老的葡萄树和夹竹桃,自他们离去愈加欣欣向荣,奶奶每年都把这些葡萄摘下几篮子分送左邻右舍,每年送葡萄是奶奶难得的娱乐活动。有些年二伯一家在外不顺,慌不择路去问算卦者。祸殃竟是那株繁花正浓的夹竹桃。然后殃及池鱼,葡萄树也被砍去,也砍去了奶奶很多的念想。奶奶离世之后,前后院的门立即封死,暗暗预示着主人离开的决心。我每年通过我家窄窄的过道侧身过去前后院,按父亲的要求给门上贴上门画对联。对联上都是寻常语,尽是家业兴旺,庭院长扫。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最后我要说说我的堂姐,我记得以前喜欢给她讲笑话,她总是投入地聆听,并格格笑个不停,让我觉得被关注且有幽默感。我对她的记忆就这么些,她的离开好像一下子把她从我的记忆力抹去。直至前些天给我打电话,问及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。她说她的工作已经给生活带来足够多的物质基础,并且非常含蓄地表达了我如果愿意去,她随时地接受我。我蠢蠢欲动,最后同样含蓄地说我目前很稳定。这个电话她很开心,对我做了很多的鼓励。我想着也许是因为通电话,彼此的变化并没有多少直观的感受以至于造成震撼。我跟她说已经十几年没见,如果再见应该都不认识了。她说怎么会呢,变化再大,还是能找到曾经的。大约是因为我的语气有点感伤,她好像是母亲安慰儿子的口气,说着不怕不怕。
以前很多的时候,我对他们的杳无消息颇多地腹诽,后来我想大概是他们都活得太骄傲,我心里有羡慕嫉妒恨的心思在作祟。现在我突然很理解。他们在外面买了房子,成了家庭,立了事业,识了新人,你不能要求他们对过往不停地去追寻,去感受。一个朋友跟我说,有些人是需要垫底的,埋藏到最深处,要不然你的行囊里会负载太多,不利你大踏步的前行。而且当你活出一个不同的境界的时候,你会发现曾经的同伴已经隔得太远,远到你懒得打一个电话去问一声安好。
我想,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安身立命,另一方土地,留给回忆何尝不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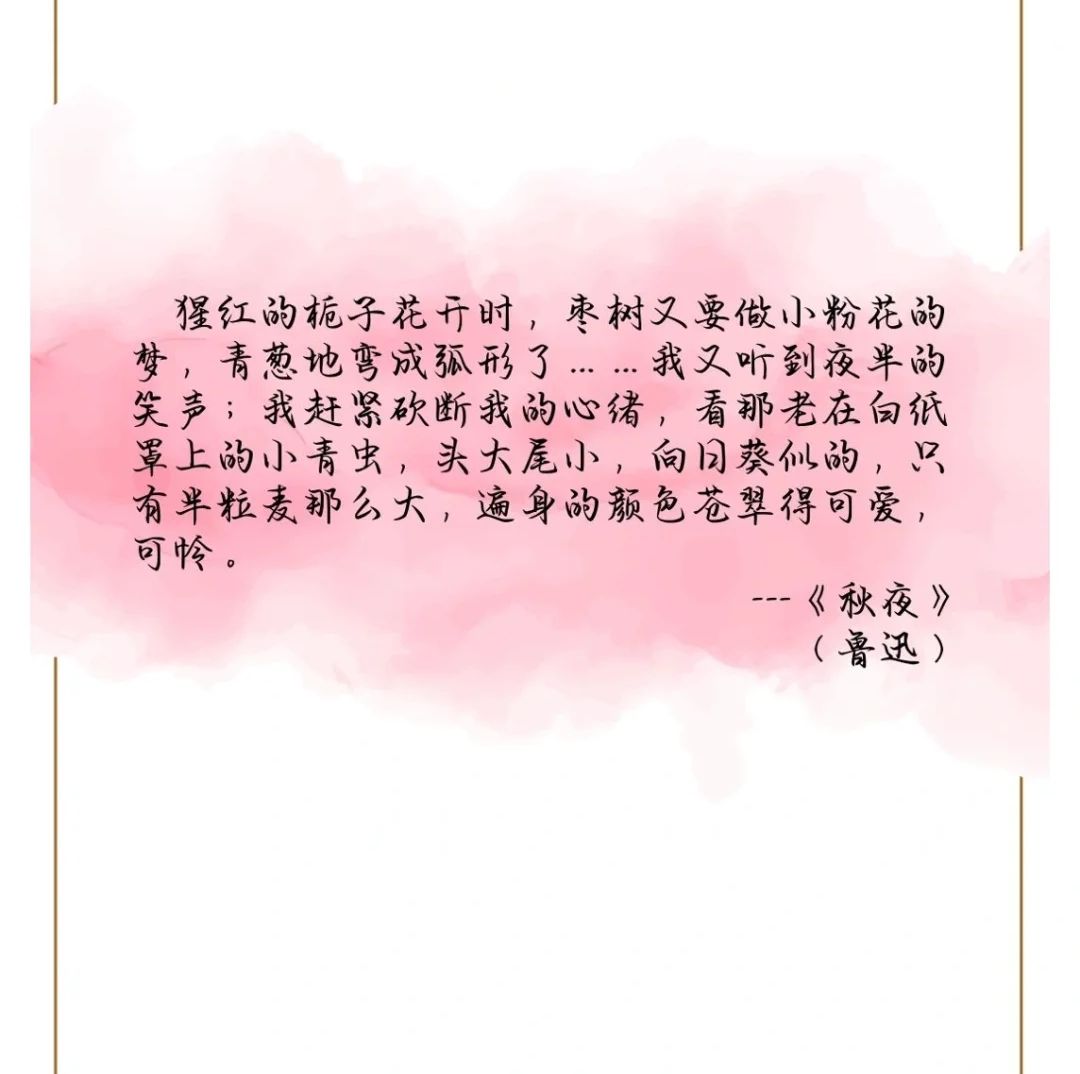
请登录之后再进行评论